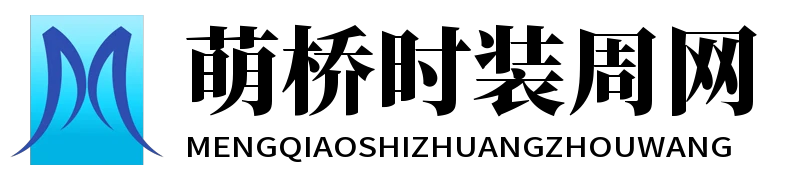在我生命的六十多个春秋里,这是第一个没有彭小莲的春天。她走了快一年了(彭小莲, 1953.6.26—2019.6.19)。八十年代初,我正沉浸在英文语法书中,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抬头一看,小莲已然站在门口,她那灿烂的笑容如同阳光般温暖,“你在看什么书啊?” “英文语法。” “喔唷唷,这种书我是不会看的。哎,我们去小学看看杨校长好吧?”

童年、少年时代的小莲虽然我们未曾相遇,但她的名气远播。我听闻她与街坊无赖扳手腕时,那凶狠眼神;她与男生合唱,情意绵长;她到江西插队,体验贫困生活;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,都让我印象深刻。那些传闻真假参半,但它们让人不禁感慨:即便身处逆境,她依旧保持着大胆和张扬。
插队岁月,那十四五年的日子,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变故最多、磨难最重的时期。但我们活到了今天。在这段时间里,小莲展现出了她的率真和活力,即使时间流逝,她仍旧如此美丽和充满活力。我们的友谊如同树木一样,不受岁月侵蚀,我们之间的情谊依旧那么坚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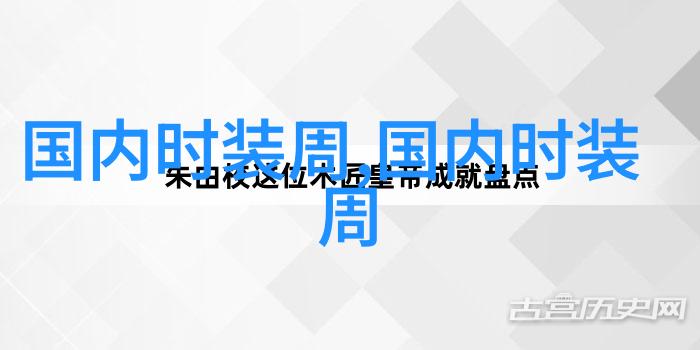
八十年代跟谢晋导演一起工作1982年,小莲从北影毕业,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。那时候,我正在美国求学忙碌着硕士和博士研究。我是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中文杂志上偶然看到小 莲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《黑夜白昼》,读完后,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祝贺。不久后收到了回信,只记得结尾的话:“好好的啊,活出你自己。”这样的强烈个人意识,在那个时代不常见,可我却把它置之脑后,将目光投向世俗的事务直到有一天,当一切似乎顺利的时候,我突然感到恐慌。这促使我开始自救,从图书馆借阅大量中文资料,看遍所有关于文学创作的小册子,其中包括小 莲作品《阿冰顿广场》、《燃烧的联系》等。她以独特的声音讲述故事,让读者陷入梦幻世界,却又带有压抑、焦虑的情感。她用朴实无华的话语记录下历史与人生的真实面貌,其中也包含了她的个人经历。
九十年代再次相聚是在1996年初,当时,她刚从美国留学返回上海,而我则因学术休假而回到中国陪伴我的母亲。那是一次意外惊喜,因为就在我抵达上海前两天,小 莲就给我妈妈打电话询问近况,并留下了电话号码。我赶紧拨通电话,与过去几年的隔阂一扫而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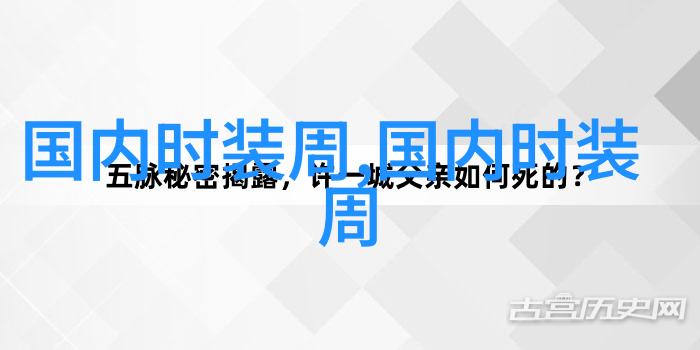
九十年代末拍摄《上海纪事》之后,我们重新找到彼此,就像往昔那样紧紧拥抱,每个人的变化都被细致地观察过。在一次简陋饭店里的午餐时分,我们谈论起为什么她决定回国。她说:“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任何遗憾,我一定要回来陪她。”当然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对电影艺术深深的情怀,以及回到国内能更好地进行拍摄。而且,她爱文学,更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故事,它离不开中国文化土壤。这之后二十多年间,我们一直保持联系,频繁交谈,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感纽带。
九十年代末拍摄《红日风暴》期间,小 莲展现出一种“真”的执着。在这部关于胡风分子的纪录片制作过程中,她付出了极大的心血,又花费巨资。但对于这些付出的辛劳,她始终缄口不言。这是一个选择,是为自己的历史定位,也是承担起沉重的心理负担。一路走来,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或社会潮流如何变化,小 莲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,用实际行动去追寻那些真正值得珍视的事物,即便这样做让她的内心承受巨大的痛苦也是如此。